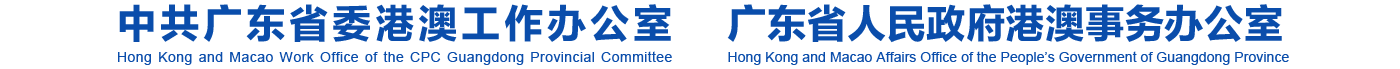千余年海丝起点,百余年革命薪火,四十余年改革先行,自古以来,广州一直领改革风气之先,勇立开放之潮头。当下的广州,正在积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继续在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领头羊和火车头作用。
广州南沙,地处大湾区地理几何中心,是广东通往海洋、走向世界的重要门户,广深港、广珠澳科技创新走廊在此交汇。去年6月,国务院印发《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下称《南沙方案》),提出将南沙打造成为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意味着南沙将在国家省市发展大局中,承担起更重大的使命。
4月28日,由广州市社科联、暨南大学、南方日报社主办,中山大学区域开放与合作研究院、《城市观察》杂志社、广州市舆情大数据研究中心共同承办的第53期“广州新观察”学术圆桌会议召开,邀请政、企、学、研各界专家学者,围绕“加速南沙开放开发 打造高质量城市发展标杆”建言献策。
把握定位 提升开放能级
2023年广州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坚持面向世界、对标一流,以南沙为牵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报告首次提出了南沙的新定位——建设成为广州城市新核心区。
南沙作为广州的开放门户,定义和衡量“开放”成为关键的课题。
如何才称得上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科研部主任、研究员叶辅靖给出了六个方面的衡量标准。“首先是要实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二是开放的质量要高,比如合作伙伴档次高、资金盘活能力强、产品和要素市场质量好、人才高端实用等;三是开放的规则要科学、先进、公平、合理;四是开放的壁垒要少,便于商品、服务、数据、资本、人才的自由流动;五是开放的管理水平要高;六是开放的作用要显著。”
目光回到当下的南沙,“2022年形成108项制度创新成果;累计开通18列中欧班列;南沙综保区获批最高等级A类;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12项落地,交易金额累计达176亿美元……”南沙开发区(自贸区南沙片区)党工委副书记谢伟从制度创新、航运物流、国际贸易、特色金融等方面介绍了南沙在提升对外开放门户枢纽能级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
开放已成共识,如何进一步实现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是“南沙实践”要持续探索的道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港澳台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任志宏为此提出,“在兼顾发达国家的同时,要大量与发展中国家对接,在此过程中,南沙应笼络高端智力资源,在开放中体现自身的标准、规则、体系;南沙的开放要逐步向服务环节转移,比如电信服务、咨询、养老等,都是未来深耕的方向;此外,南沙要着力打造以减少交易成本、交易费用为主要特征的开放。”
作为广州“双核”之一,牵引带动全市制度型开放上新台阶新水平是南沙的重要使命。
“规则和供应链联通,可以使全球GDP增长5%,因此在开放中非常重要。南沙有世界级的供应链,可以联通中国和世界的供求市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院长申明浩从制度与规则衔接的角度进行了探讨。
申明浩指出,粤港澳合作的几方面是钱跨境、税平衡、人往来、数据流动。其中,数据流动是难点所在。“南沙可以作为数据跨境的试验区,短期目标是实现数据跨境赋能机制,中期目标是完善数据跨境的规则体系,长期目标是提升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以“海”为核 从浅蓝向深蓝
《南沙方案》高规格出台,对南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向新定位,南沙将打造成为全球海洋科技创新策源地、国际航运枢纽核心功能区、全国海洋新兴产业集聚区和现代海洋服务高地,未来将基本建成广州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核心区。
向海图强,向海图兴。“海”成为南沙实现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的前沿阵地。作为广州由江入海的门户,南沙该如何迈向深蓝?
在山东大学商学院、自贸区研究院副院长杨林看来,南沙虽然正加速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但海洋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也面临困境。
“南沙的新兴海洋产业规模小、比重低。”杨林认为,在南沙,海洋服务业仍有较大发展提升空间,海洋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较低、经济发展贡献率低;相较其他地市及区县,南沙近海海域面积较小、岸线人工化程度高,可供开发利用岸线尤其是深水岸线资源紧缺,亟待进一步向深远海拓展空间;此外,科技与金融对海洋产业的支持力度有待加强。
对此,杨林从产业结构方面提出了建议。聚焦第一产业,南沙应发展水产种业,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支持东涌、万顷沙片区搭建海洋生物产业服务平台,打造海洋生物产业集聚区。第二产业方面,南沙要大力发展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国家科技兴海产业示范基地。针对第三产业,南沙应深度提升海洋服务业价值链水平,例如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国际航运服务业,加快南沙港区四期自动化码头建设,充分利用园区已有铁路,进一步提高港铁联运能力。
南为海,北为陆,南沙位于海陆连接之处。得此地利,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王世福认为,“南沙是整个国家走向海洋的门户和枢纽,广州海的文章就在于南沙。”
“沟通东西、联络南北,无论是顺德、佛山,还是中山的出海口,都会受到南沙枢纽的联系,它们通过南沙走向世界。”王世福说,南沙港成为海洋文明和陆地文明再次交汇的枢纽。而南沙面向未来的实践,也正在以“海”为内涵,进一步谋求从空间到产业上的高效转型,“最后实现从广州的南沙,走向世界的南沙。”
要素齐聚 打通关键环节
南沙,这一广州城市新核心区,正在打造一座高质量发展的“新城”,从产业体系的培育,到精致城区的建设,都需要强化各类要素的保障。
在广州技术产权交易中心总经理、华南技术转移中心董事刘伟看来,知识产权的发展围绕着科技创新、人力资源、金融、产业四大要素。对南沙而言,数字标准的建立是关键一举。
为此,刘伟建议南沙积极推动知识产权数字化应用,借助专业知识产权数字化智库,构建存量筛选、增量标识、项目预估、价值判断、产出分析系列化应用,助推区域经济更大开放、更好搞活。同时,打造联动互济开放生态,对内以知识产权转化运营为轴心,串珠成链、共营多赢;对外联动海陆,东西互济,形成多链融合的生态。
“大湾区是中国建设世界级人才中心和科创高地的重要地区,南沙又是其中的关键核心点。”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粤港澳大湾区跨域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杨爱平认为,在南沙的发展图景中,人才建设已刻不容缓。
针对南沙现状,如何因地制宜做好人才工作?杨爱平提出了三组“平衡”。
首先,要平衡人才的量和质。“南沙首先要追求人才的量,然后再讲质,从人才生态链发展的角度,南沙应在聚纳人气、汇集人流的基础上,追求国际化高端人才的引进。”其次,要平衡国际化人才和国内人才的关系。南沙应利用广州高校人才聚集的优势,着力吸引本地高校人才。此外,也要平衡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搭建平台,营造环境的同时,要平衡市场机制本身的合理调节。
“金融的天职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在广州市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所长蔡进兵看来,南沙的一项重大任务是让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金融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南沙的金融应如何担此重任?
蔡进兵认为,首先,南沙要与港澳实现金融互联互通。例如怎样打开到港澳投资的通道、民生金融的堵点如何打通、三地间的金融数据怎样更好流通,都是应解决的问题。其次,广州的金融基础设施应进一步辐射南沙,南沙现有的金融交易平台也应持续提升影响力。此外,在特色金融方面,南沙可以做更多尝试,比如加快推进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